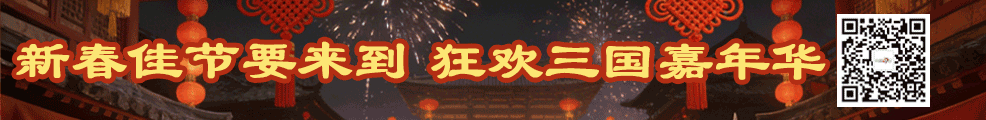七 透过现象看本质
午饭过后,饭盆也很快被别人洗完了。
没有人午休,也没有人吭声。在这一小段真空时间,我能感觉到,服水土这一关是躲不过了。
有人问话了:“因为甚进来的。”
“打架打死人了。”我尽量营造出在漫不经心中表达出自己手上有人命这一事实。毕竟,我杀过人啊!你们不畏我三分么?
“杀了几个。”继续是平淡且真正漫不经心的腔调。
“一个。”
一听只有一个,问话者略有失望,扭转过头再也不问了。毕竟这是上马街啊!他们见过的杀人犯太多了。只死一个说明过程不会有多惊险刺激曲折,也就没人爱听。我有些沮丧,脑海中霎时浮现出“当时怎么不多干死几个,免得现在让人小看”的念头。
过来两个年轻人。一个是刚才洗饭盆的。按惯例他应该是在我之前最后进这号子的,我来了我擦地,他被顶起洗饭盆。另一个是刚才给戴镣者捏腿的。不消说也是板油一个。洗盆者身高一米六左右,算得上敦实粗壮,脸上全是粉刺,好大的粉刺啊!其中一个都快把嘴角的酒窝填满了。捏腿也只有一米六左右,瘦马鬼筋。不是吹,就他俩这样,我顶在墙上任他们打,他们也不一定能打翻我。
“知、知道规矩么。”捏腿者还是个小结巴。
“知道。”
“顶好!”
“我在南看已经住了一年了,身子都住穰了,你看……”我试图摆个架子。
“一年?你看这儿的哪个不是住了一年以上的!顶好!”
看来这一套行不通。我原以为他们这话只是用来搪塞我,后来才得知所言甚实。在上马街住了一年号子的比比皆是,住两三年才敢自称是个老犯人,居然还有一个住了八年判不下来。这些以后再说。现在我先顶好。
我顶在木头号门上,不疼。没人要求我做到“雁飞”,我也就顺势偷个懒,只是普通地弯下腰,头顶门。
“嗵!嗵!嗵!”几肘砸在我背上。太小儿科了!我身高一米八出头,虽在南看一年来食不裹腹而面黄肌瘦,但骨架子毕竟放在那儿。就他二人这力度,和我比差远了。
“嗵!嗵!嗵!”又是几下,还是肘子。没有脚肘,没有通心肘,看来这俩后生道行不深,既没掌握打人的要领,打人的欲望也不强烈。我顶在门上,背后不疼不痒地挨着肘。回想起在南看时给别人服水土的情形,从内心深处蓦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想打人的渴望。我太想打人了!就现在!
但我不能,我不能服股(反抗)。不过,也得表示一下,不能一味挨打。
我直起身:“在南看把身子都RUA疲了,差不多就行了吧。”
“少****扯这些,顶好!”捏腿者不依。
但我并没有立即弯腰顶下去,而是笔直地站着,冷冷地扫了他一眼。
我以前没服过水土,也害怕上马街,但现在已经来了,也服开水土了。既然命运要让我在这儿熬一段时间,我就不能甘于当个最底层的板油。就算我目前只能做板油,我也要做个有尊严、不能让别人小瞧的板油。想到这儿我怒从心头起,恶向胆边生。估计我当时的脸色很难看。我脸大眼小肤色黑,虽有眼镜彰显我文化人的身份,但镜片后的小三角眼一扫,他们应该能体味到“狰狞”之意。
但是,我还是服软了。三五秒的僵持后,我还是顶下来了,因为我深知自己没有任何实力去服股。不服股,只能服软了。我顶在门上,等待着水土的再次到来。操!就算你们几个一起来,也扯老子的旦!
“算了。”有人发话了。是戴镣者。我直起身,依旧挺拔,淡淡地看着他,不因为他停了我的水土而流露出对他的服从感激和谦恭。
水土结束了。
洗盆者告诉我擦地布子放在哪,如何擦,擦到什么标准。其实这是勿庸多言的,我在南看就是从洗马桶擦地干起来的。在这儿最板的板油只擦地,没马桶,一天放两次茅,大便就在茅房,平时在号子里小便时就在水池里,一边尿一边用水冲,根本不会有臭味。号子里现在有八个人,通铺上睡六个,我和洗盆者睡地铺。他姓张,叫张翼德。张翼德?这个名字让我不由得多瞅他几眼:矮胖的身材,蹩脚的普通话,满脸的粉刺,这不是纯粹玷污了我心目中猛将张飞的高大形象嘛!
事后,一次只有红军和我单独在一起时,他说:“当时我已经表示出认识你了,就想着水土就免了。没想到他们还要动手。后来我见你直起身,以为你要股。你要是股了收拾那两个小的没问题,别人要是敢上,我就翻脸跟他们干!”
我淡淡一笑:“没有事的,这水土差远了,况且规矩嘛!有点水土也是好事。”
红军表示非也,在南看时保全和我对他不错,现在我来了,怎么也要照顾一下,但那人(戴镣者)不给面子,给我服水土时他没有制止。这使得他自己脸上很是挂不住。
给不给我服水土,服到什么程度,这折射出这个号子里两个大油影响力的竞争。看来,凡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 |